我至今还记得,黑暗中你那双布满老茧的手。

——题记
如果说黑夜是一种寂静的美丽,那么对我来说,就是一场无声的葬礼。每到夜幕四合,我就会把房间弄得灯火通明。如果停电,我宁愿在被窝里发一晚上的抖也不愿去找蜡烛。
因为,我怕黑,黑夜的黑。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我那装满吊灯的房间。那是怎样的恐惧和绝望啊?我甚至不敢去回忆,那种身不由己的无奈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不能用它去寻找光明。
走进寝室,那两盏日光灯,好像是上帝少得可怜的怜悯。我没有选择,只有接受,试问,又有谁会在意我的哭泣?我甚至没有看到同寝的室友那疑惑的神情。我连招呼都不敢打,自卑是个女巫在用她的魔棒将我和世界隔离。还记得,小时候看过一本书,上面说:夜盲症是喜爱黑暗的巫婆送给在太阳落山时出生的孩子的礼物。多可怕的诅咒,我刚买的棒棒糖碎了一地……
刚来那几天总是一关灯,我便会神经质地大叫,或是像受了惊的野猫一般在被子里弓着身子,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渐渐地我成了班里的异类。但我还是庆幸他们不知道,我看不见,最多只是以为这是一个未满十岁的孩童的恶作剧罢了。
那种无论是闭上眼或是睁开都找不到一丝光明的感觉,别人是体会不到的。就好像眼睛被销蚀了,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装饰品。那种灵柩般的阴霾,那种从骨髓里腾空抽出来的空虚。全身像被置放在了一个冰窖里,不能动弹,不能出声,仿佛连心跳都被禁止了,蜷缩都没了力气。我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,什么也没触到,但好像有无数的东西包裹着我的手,那么冷,那么不真实,那些让我不寒而栗的魅影!就在下一秒,我毕生都不会忘却的温暖,就像把求生的人从死神的手里拉出的神祗。那一刻,我触到了阳光跳动的脉搏。不同于冷冷的日光灯。它是有温度的——像母亲的体温。但不觉地,一股心酸涌进我的喉咙。在我手里放着的`,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?那么小,指节犹如新生的竹笋,稚,却不嫩。她的手让我想起了外祖母那辛苦了半百个世纪的麻布般的老手。她都做了些什么?竟敲磨出了这样一双与一个9岁孩子那么不相称的手。我把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脸颊旁摩挲。细密的老茧咯地我脸蛋生痒,但我却哭了,断断续续地啜泣。泪珠划过脸庞,沁入她的手掌里。她就那么轻轻地颤了一下。最后,归于平静……
那一夜,我们就紧紧握住对方的手,直到清晨的第一米阳光撒在我的脸上。原来就算上帝不愿赋予我黑夜的眼眸,我也能自己去拥抱光明。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和惊天动地的友谊。我没有为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而和她结下一段不解之缘,也没有为那一夜如昙花一现的温暖而战胜黑暗。因为那一夜,恍惚如神迹一般,我看到了那双眼睛不是渗透深沉色彩的理解,而是属于童年最纯真的给予。
如果记忆是一个华美的匣子,那么我愿用世上最怜惜的花装点那份纯洁,让它永远沉于盒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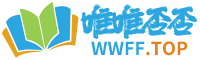
 粤公网安备 440106xxx4424
粤公网安备 440106xxx4424